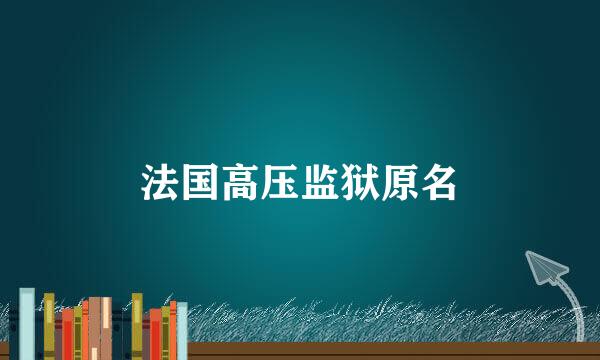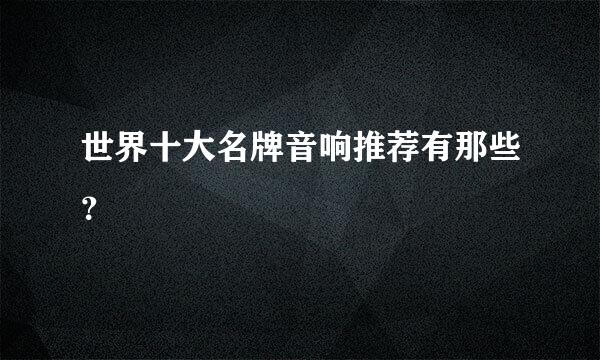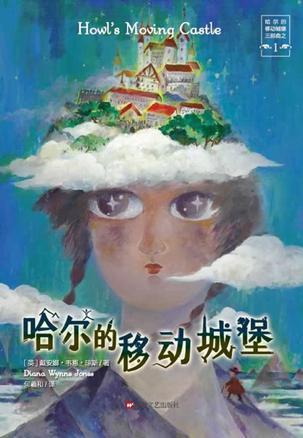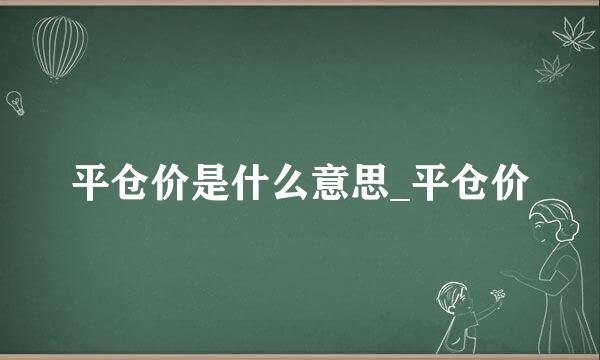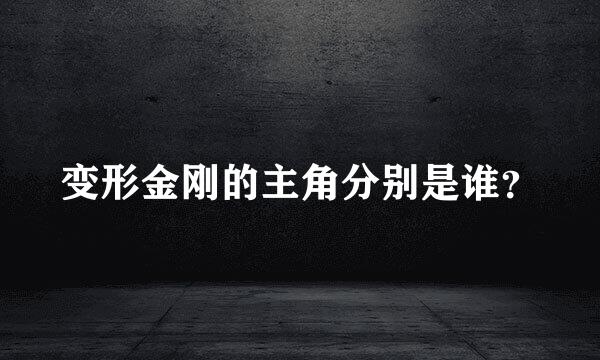董玉飞之死的隐喻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值此光景,不由人叹一声“时光何其荏苒”,虽然我们的胸口仍在隐隐作痛,不知不觉“5·12”汶川地震发生距今已有近半年之久。托体同山阿,多难寄兴邦,挥泪揖别举国同悲的国殇,或许是到了我们重新振作精神,去面对未来的时刻。 但就在同一天,另一则也与震灾相关见于《华西都市报》的报道,却足以使得我们再次潸然落泪。据悉,日前一些帖子在网络逐渐流传开来,大家都在传播、讲述一个难过、痛心的事实: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10月3日已在暂住地自杀身亡,他是历誉北川灾后首例轻生的政府官员。 “作为一个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救援者,老董走得让人很痛心”,北川县委如是评价董玉飞之死,这一点,无疑也是毫无意外地令我们备感痛心的原因所在。我们的确很难去接受这样一个莫大的悲剧事实:一个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救援者,最终却又自选成为了殉葬者,当昔日不屈地抗拒着的死亡成为了其解脱方式,这其中究竟又隐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沉重与悲哀呢? 据报道,关于董玉飞之死,存在着两种说法。一是说他因为痛失爱子和众多亲人难以自拔悲伤过度自杀。这话我信,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若非亲身经历,丧子丧亲之痛究竟痛若何般,我们是无法理解的。二是说他工作压力太大、实在是想好好休息,据称这是董玉飞遗书里的内容。这话我也信,假如不是亲眼目睹灾区惨状何极,不是亲身挑着灾难的担子,其工作压培镇力究竟有多大,以至于想凭借自杀而“好好休息”,这或许是作为关注者却至多只算是“局外人”的我们更无从体会的。 当然,斯人已去了,再一本正经去追问、揣测董玉飞之死的具体原因何在,这肯定是不妥的,也无异于在其之前就避开媒体视线的亲人伤口上“撒盐”。事实上,不管是死于丧亲,尤其是“白发人送黑发配烂粗人”丧子之痛,这一亲情不能承受之重,抑或是死于“工作压力太大”的使命不能承受之重,透过这两个具体原因的个体因素,我们不难看到的是:董玉飞之死所告诉全社会公众的,不仅是一个个体生命于“生存还是毁灭”之间的终极抉择,就普遍意义而言,它更是诉说了一个关乎地震灾区人们生存实况的悲剧性隐喻:亲人不在,何以慰藉?家园不在,又何以重建? 笔者犹记上个月看到的两则消息。一则是9月18日《南方周末》披露:“至今四川灾区的88名残疾孤儿无人问津,其中60多名残疾孤儿的原定收养者甚至临时取消了收养意愿”。另一则是23日四川副省长黄小祥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四川灾后重建需要1.6亿元的重建资本,但目前各级财政、对口援建、社会捐赠和一些特殊的支持,加起来能够提供的重建资本大约占所需的不及百分之二十五”。在这里,我们似乎更能“理解”董玉飞为何选择了死亡,也才能“理解”他同事的那番看似突兀言语——“董玉飞同志的自杀是偶然的,但我们不能漠视这种偶然。因为,这既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更是对活者的不敬重”,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笔者看到,在报道的结尾,记者只写了一句话,意味深长:“但愿董玉飞的悲剧,是灾区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此言不谬,若能如此,我想,灾区溘然而去的千万个逝者当瞑目于九泉之下,茕茕孑立的悲痛生者亦可康乐于有情之此岸,董玉飞用其生命写就的隐喻,算是得其所值了。
标签:董玉飞,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