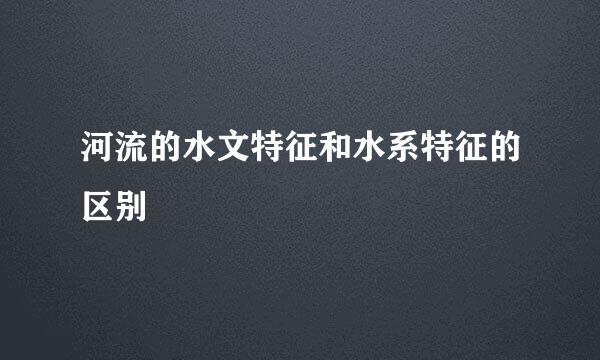流行语是一种词汇现象。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是一种词汇的分类研究。所用词汇一般有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特点。流行语,作为一种词汇现象,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和事物。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行语,而不同的流行语则作为社会一根敏感的神经,反映出社会的变运丛仿化。伴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很多新思想、新事物,而“流行语”正是这些新思想、新事物最好的见证。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还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够涌现出这么多的流行语,那么集中、大量地丰富汉语的词汇。现如今,每一个经过改革开放岁月的中国人,随口都能说出几句改革开放的流行语。“流行语”昭示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到“不管白猫黑猫,旁纤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出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曾几何时,凡是先哲说过的话就不能改变,凡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许违背,被小人物的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搅了个底儿朝上。从此,是真理还是谬误,不再看是谁说的,而要看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至于好与不好的区分,不看你说得如何,也不管你出身贵贱,而只看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事——“不管郑樱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同样,这道理,那道理,不发展就没道理;这有理,那有理,经济社会发展不上去就是没道理。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回想当初它们是怎样打破了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思想的禁锢,产生石破天惊的效应,就会发现解放思想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值得珍惜。“流行语”昭示了社会的进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提出,到“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标志着科学重新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标志着搞建设、办企业开始注重科学性,不再盲目蛮干。昔日的动辄“加班加点”、“大会战”、“为节日献礼”等只求数量不讲质量、违背科学的举动开始为科学精神让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更是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定下了科学的基调。这些流行语告诉人们,科学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向有利于人类子孙后代生存的长远发展,是毫不掺假的真发展,而那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违背科学、违背自然规律的所谓“发展”,将被等同于“破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憎恶。瞧,同30年前相比,社会是不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流行语”昭示了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提升。这30年,特别是近些年来,“民生”、“以人为本”、“群众满意不满意”、“关注民生”、“民心工程”之类的词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中。可以说,有史以来,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民生,把老百姓这么当回事儿。在今天的中国,民生成了全中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民生?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生计;复杂一点儿说,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一句话,就是要让老百姓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如果这些事政府都给解决了,老百姓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当然,不能把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停留在这样的程度,更不应该满足于只是“有”的低水平。问题是,只有先解决了这一步,才能说下一步啊!再说了,这一步迈出去了,下一步还远吗?毋庸讳言,改革开放的流行语除了较多的颂言赞语,也还有讽喻和微词。常能听到看到的就有“边腐边升”、“几十个图章管不住一张嘴”、“形象工程”,以及那句人所共知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等等,极为形象地道出了人们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不满和反感。这说明,生活中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尚需进一步完善。换个角度看问题,这些不满的词语得以流行,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倘若政府容不得不满情绪、听不得不同的声音,这些不满的词语又怎能成为“流行语”?流行特性流行语的本质特性是“流行”,因此流行性是流行语的本质属性。“流行”是针对“不流行”而言的,时间性是“流行”的第一个涵义。换句话说,流行语都有一个从流行到不流行的过程。流行语的发展前途只能有两种:一是消失,即在使用中被淘汰;二是被接纳,进入一般词汇。第一种前途说明流行语是一个历史范畴,昨天的流行语不等于今天的流行语,甚至连今天的一般词汇都不是,换句话说,已不属于现代语言的词汇系统,只具有历史词汇的身份。比如北京话的“盖”,上海话中的“阿飞”等。流行语是一种动态现象,产生、消失或被接纳都有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可以有长有短,甚至有些新词新语本身就是作为流行语而创造的。处在这种过程两端的流行语,前端与新词新语、后端与一般词语容易混淆,这就给流行语的定性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流行语的其他属性。“流行”的第二个涵义是阶段性,一般来说,流行语的“流行”过程是比较短暂的,或者说短暂性是流行语时间性的一个特点。当流行语使用一个时期后,就会消失,如果没有消失,而在这个流行层面达到一定的普遍性时,比如作为北京、上海的地域流行语在北京、上海区已经相当通用的时候,并逐渐失去新鲜感,使用的频率相应降低的时候,流行语就进入了地域方言,成为当地方言的一个普通词语,尽管它们来源于流行语。比如“二百五”“没戏”(北京),“十三点”“炒冷饭”(上海)等,这些当年的流行语早已成为一般词语。像“路子”“翻船”“二进宫”等还进入了书面语。有些流行语只在中老年中使用,也早就失去了流行语的性质,如上海话的“兜得转”“掮木梢”等。可见,“流行”几十年的流行语是没有的,老的流行语总要被新的流行语所替代,如北京话表示“好”的流行语由“棒”到“帅”到“盖”再到“顶级”,上海话表示“乡下人”的“阿乡”为“巴子”所替代。被替代的流行语或消失,或进入一般词汇。“流行”的第三个涵义是高频性。流行语的使用频率比一般词语要高,是一段时间内群众所喜闻乐用的。比如北京话的“打的”“倒爷”等,上海话的“捣浆糊”“勿要忒”等。高频是针对流行面而言的,上面几个流行语都具有地域性,在地域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而像北京话的“潮”“栽”等,上海话的“门汀”“条子”等,只在社会方言的层面上具有高频性,换句话说,只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具有高频性。高频性还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因为流行语的“流行”都有一个过程,而且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修养、不同语言习惯的人使用流行语的态度也不相同,流行语的使用有很大的选择性,高频只是相对于一般词语的平均使用频率而言的。“流行”的第四个涵义的新型性。因此,流行语必然都是新词新语,或者说新词新语是流行语的基础。但不能反推,因为新词新语并不一定都是流行语。比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急遽变化,必然会涌现大量表示新情况、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新语,如“创收”“个体户”等,这些词语虽然也具有新型性,但只是一般词汇,而不是流行语,因为它们还缺乏流行语的其他特征。“新”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结构新,比如北京话的流行语“玩一把”“爱你没商量”等,上海话的流行语“勿要忒”“拎勿清”等;第二是语义新,比如北京话的“铁”“款儿”等;上海话的“(一粒)米”“大兴”等;第三是感觉新,因此不少流行语借自外地方言或外国语言,比如北京话借自港台的“酷”、借自东北方言的“造”、借自英语的“ByeBye”等,上海话借自港台的“大哥大”、借自北京话的“斩”、借自英语的“达孛留西”等。层级层次从流行语的基本属性及其通行范围来说,将它限定为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的性质显然是不恰当的。一般来说,流行语常常发源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但不等于说流行语只属于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像“国脚”“前卫”之类的流行语是由书面语转化而来的。当地域或社会方言的流行语使用的范围逐渐扩大,经过书面语的过滤,就可能成为普通话的流行语,比如“大哥大”“买单”等。普通话中的流行语无论发源于书面或地域或社会方言,加起来数量也是有限的,这取决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流行语的性质,经过书面过滤,能进入普通话就不多。判定一个地域或社会流行语是否进入普通话,有两个标准:一是看书面上是否经常使用,这里所指的“书面”不是指一般的书刊杂志和文章,因为各地的出版物为了突出地方特点,大量使用方言词语。因此我们所说的“书面”是指权威性的报刊杂志和比较严肃的文体;二是看全国主要方言区域在书面和口头上是否使用。普通话的词汇是吸收全国各地方言土语的词语来丰富发展自己的,因此吸收流行语也顺理成章。流行语基本上发源于地域或社会方言。我们将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并提,并不是说它们是并列的,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方言不是普通话的社会方言,而是指处于地域方言层面上的社会方言,于是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就处于包蕴的关系,地域方言是各种社会方言的总和,它们处于不同的层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语是发源于各种地域社会方言。比如有些流行语起源于俚俗语,原先只通行于社会的底层群体,或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如北京话的“顺”“T”等,上海话的“冲头”“煤球”等;有些来自学生或普通知识群体,如北京话的“跟着感觉走”“平常心”等,上海话的“开天窗”“背猪猡”等;有些来自青少年,如北京话的“小菜儿”“飒”等,上海话的“牙大”“吃转”等;有些来自黑话,如北京话的“趟路子”“雷子”等,上海话的“打野鸡”“老头子”等。随着使用的扩散,这些社会方言词就成为地域方言的流行语。因此可以说地域方言的流行语都来自地域社会方言,但地域社会方言词语却不一定都是流行语,因为大部分社会方言词语只使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比如北京话的“考研”“刷课”等,主要使用于学生群体,“放血”“折”等是使用于流氓群体的黑话;上海话的“门汀”“一粒米”等是商贩的行话,“庙”“堂子”等是流氓集团的黑活。由此可见,当一个词语仅仅是一种社会方言,与一定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时,它们只是一种行语、“切口”或黑话,不具备流行语的性质。只有当这种词语在使用中发生扩散,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所使用时,才逐渐发展为流行语。比如北京话的“碴舞”“蹦迪”原来只是学生的“同行语”,“雷子”“底儿潮”等原来是黑话,后来发展成北京地域方言的流行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即有些历史上的流行语,早已不流行或不使用了,但随着某些社会现象的出现,这些旧的流行语又重新流行起来。如“鬼市”“走穴”(北京),“小房子”“仙人跳”(上海)等。一种社会方言词语是否成为流行语要使用上文提出的流行语流行性的四种涵义来衡量,看看它们是否已经具备了“流行”的性质。衡量一个词是否“流行”会有一些困难,但处于“两端”的情况区分起来是容易的,只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词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表明了一种过渡或发展的过程,无论如何定性,都可以加以说明。 根据上述的讨论,流行语从流行的范围来说,只可能存在两个层次:一个是普通话的流行语,具有全民性;一个是地域流行语,具有方言性。这是从流行语的整体性而言的。从流行语的个体来说,无论普通话的流行语还是地域流通行语,不同流行词语的流行范围不可能是完全等同的,同样体现一种层级性。但不管这些流行语的流行范围如何,它们比起同行语来,通行的范围要大得多,使用频率也要高得多。比如北京话的“撮”“T”等主要流行于社会和文化层次较低的社会群体或所谓的“痞子文学”;上海话的“三妹子”“叉模子”等主要使用于文化层次较低的青年工人、个体商贩等。从流行语的发展来看,通行的范围是逐渐扩大的,每扩大一次,就是过滤一次,从数量来说,也就减少一次,因此越是通行面广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换句话说,层次越高的流行语数量越少。普通话的流行语主要来源于地域流行语,而地域流行语则来源于地域社会方言。因此,地域社会方言的一些特征,往往成为流行语的一种附属特性。于是研究社会方言的这些特性就与流行语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标签:流行语